
Penana
search
Loginarrow_drop_down
Registerarrow_drop_d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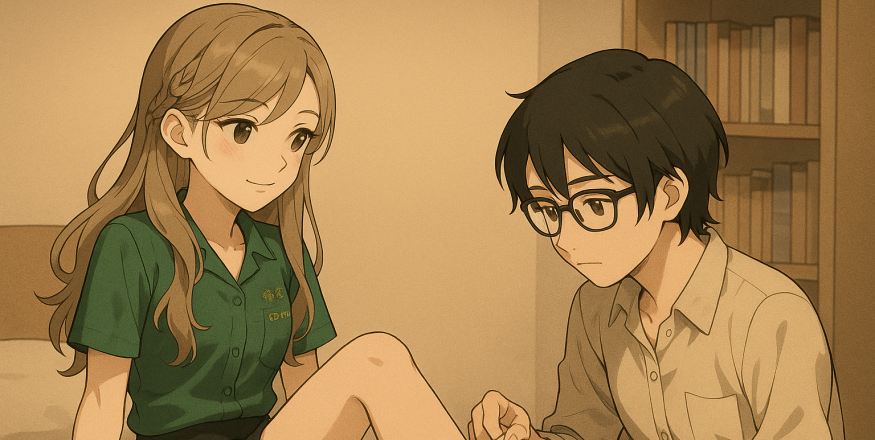





 Login with Facebook
Login with 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