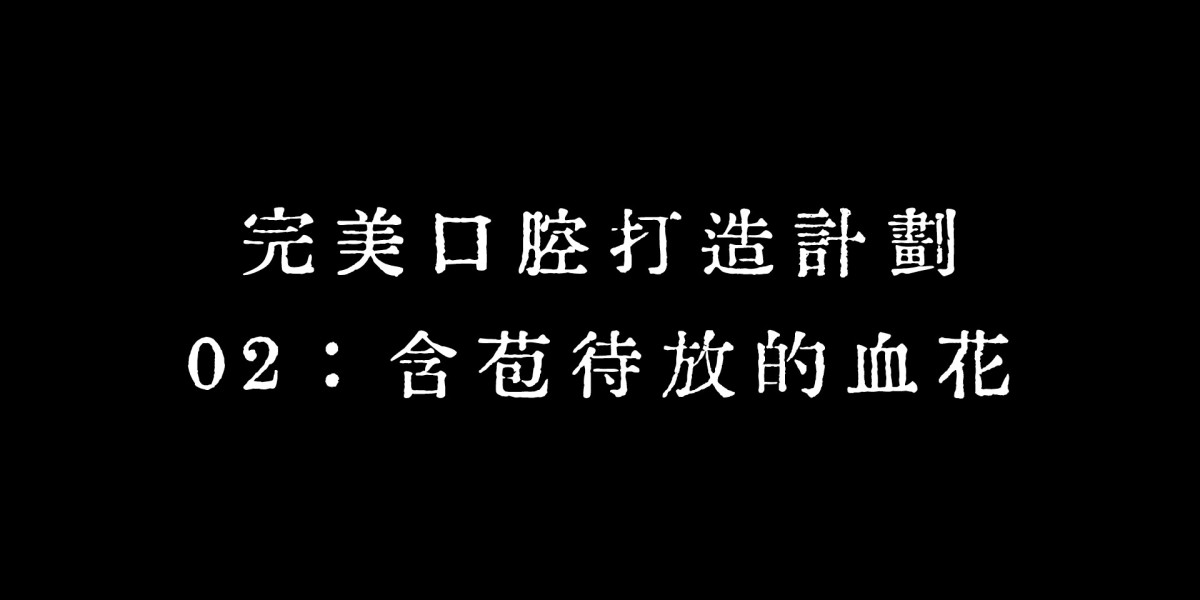 x
x
點滴注射催產素,陰道塞劑促使子宮頸軟化,迎來迷失時間的陣痛,作死胎引產。
縱使胎兒無生命迹象,還是得用力推擠,岔開腿半躺,獨個鬼哭神嚎大半天,連想有個依傍也無臂膊可攙着,憋足勁攥住床邊護欄,只為了娩出死嬰。等到那坨初成人形的原生質從胯下滑出,已經痛到無感了,反正不是肉體上的痛,任憑金屬刮匙深入陰道裏,除去黏連子宮的胎盤及殘餘物,為何其他新晉媽媽被送進產房,到龔亮熒身上卻變作屠房?
婦產科病房除了醫生與患者,還有幾台負責日常護理的智械仿生人,它們通身灰白,體型設計又矮又圓,臉部是黑色液晶顯示器,懂得分辨情境亮起相應的表情點陣圖,基本喜怒哀懼,怕是劣貨才通用於公立醫院。
龔亮熒背靠枕頭,蓋棉被坐在床上發愣,目光渙散,眼圈如塗了壁爐灰般青黑。
回顧往時所受的忽視、濫用、背叛、曲解、詆毀、疏離,她都是竭力克制,忍讓一下又不會少了塊肉,怎知忍到盡頭竟真的少了塊肉,肚子裏的親骨肉。懂事、能幹、獨立、盡責、堅強、深思,這些看似是優點,實為人們對她不管不顧的藉口,試問有誰曾安撫過她?
大概只有此刻坐到旁邊的仿生人,兩手食指互碰,臉上亮起哭泣點陣,將安撫患者列為日常護理的事項。由智械提供情感支援,醫生便可像個機器人似的,面無波瀾地站在床前,促請龔亮熒立刻作出兩個決定。
要不要抱着胎兒與之道別?要不要解剖嬰屍確定死因?
「雖然他只有手掌大小,但送到殮房之後,讓他有自己獨佔的屍櫃吧。」龔亮熒來不及消化悲傷,腦袋打結,答非所問,誤把死胎當成活兒交託院方照顧:「剛出生還很脆弱,我不想他與陌生人疊起來。」
「我們按程序辦事,你的孕期未到廿四週,我沒有義務簽發非活產證明書,也沒有理由雪藏嬰屍,會被運往醫療廢物收集站。」醫生語調平坦得惹人討厭,顯然是等到不耐煩了,礙於禮節才不敢當面發怒,便說東道西,故作愛莫能助地說教:「都說進入多死社會了,政府要執正,不是我說通融就通融,請你振作點聽清楚問句吧,要不要抱着道別,要不要安排解剖?」
深悉不能在官僚僵化的制度中得以酌情,龔亮熒別過臉去,打起了其他主意。
「我不用道別,抱起來會放不下的,解剖吧,至少要查出怎麼死。」
當然同意屍檢只是個藉口,讓胎兒不必馬上淪為醫療廢物,並送到屍櫃暫時貯存,便可趁着醫生不在場,繞過那台弱人工智能,循着昨夜在護工帶領下走過的路線,潛進驗屍間隔壁的停屍房。你看,龔亮熒尤其擅長在心理上自殘,質問自己的難過是否合理,盡可能加以否定,自然不再難過了,使得她能處於高壓狀態仍保持高執行力,但這算是心理質素強大麼?那倒不見得,高功能的行屍依舊是行屍,雖生猶死的閒角。
瘦骨零丁的瘋婆子,手裏掬着死胎,寬鬆病人服於身側晃擺,在馬路上赤足前進。
無人計程車迎面急速煞停,眼看電趟門自動打開,龔亮熒神情恍惚,踏着碎步緩慢地鑽入後排座椅,對着前排頭枕上的收音孔,將所住屋苑地點告知,由智械連接雲端運算最短路徑。
車子播放與真人無異的女童音:「歡迎乘搭智快樂車,助您至快落車。」
龔亮熒沒有大哭大鬧,只管垂頭凝視掌上的渺弱身胚,骨骼與血管在透薄肌膚下依稀可見,倍加謹慎地呵護,用拇指輕拂那豆大的臉蛋,搖曳雙手如同水面漂泊的瓢勺,願嬰屍安魂入夢,懷着母愛向閻王投遞。
慚愧的是她原為反生育主義者,認為不該將新生命帶來這個舊世界,無論科技發展有多麼迅速,人類只是維持社會機器運作的齒輪,如今與矽基相形見絀,變得更可割可棄罷了。自原始宗教締造文明至今,圈奴的最大謊言莫過於把生命視為某種神聖奇蹟,跟你說活着本身就有價值,那麼即使人生的填充物幾乎只剩下勞動,也要苟且偷生別去死,於是沒頭沒腦地追求着所謂的生存意義,事實是生存毫無意義。站在權貴制高點宏觀地看,我們不外乎人力資源,作為寡頭和財閥用來鞏固權力及瓜分利益的手段,生活拮据的難有尊嚴,便打開社交平台麻痹自我,在演算法的貼文推送下跌進同溫層,先分化、再極化、面譜化、大批量生產。
與其貪生不如求死,或戀上可任意支配的玩物,才不至於喪志。
真有必要把孩子生下來當牛做馬,大半輩子勞碌奔波,還得走避輻射雨的毒打?
可惜忠於自我並非易事,心裏的辯論家不免因現實焦慮而噤聲,雖則丈夫少時離家無意延續宗族血脈,但像他那種健身成癮的保險經紀,多次說要將自己的優良基因遺傳下去,龔亮熒畢竟是個順從的女子,總是勉強迎合別人意願。
龔亮熒坦承生孩子是為了個人幸福,害怕孤寡和留憾,極度自私又兒嬉。不過從驗孕棒測到兩條線以來,別管是黄體酮和動情素在體內作祟,或妊娠導致大腦灰質遞減,這些重塑神經迴路誘發母性的變態過程,確實讓她期待起來了,無可救藥地愛上在腹中受造的形骸。
看來胎兒比起母親更有想法,等不到開局就自動登出地球遊戲。
無人計程車暫時未能暢行全港各地,例如道路規劃迂回的鄉村,曾有無人車在單線雙程路遇上迎頭車輛,竟基於安全考量宕機停駛,造成大堵塞,自此只能送到村口放乘客下車。許多老村屋已改建為簡約別緻的小洋房,惟陳舊街道的景象未完全褪去,適合於不畏地處偏僻、交通困難的夾心階層租住。
踏上洋房前的石地台,左掌兜着死胎,騰出右手按入密碼打開智能鎖,推門入屋。
「老公,我把兒子帶回家了。」龔亮熒氣息奄弱道。
穿過關着燈的客廳,摸黑向着室內走廊邁步,廊道盡頭乃主臥室,幽藍燈光自虛掩的門縫透出,北極星夜主題投影儀正在輕緩地旋轉,更傳來丈夫的悲鳴哭喊。陷於失胎之痛尚未平復的龔亮熒,依然眼神空洞,費解為何哭得那麼淒厲,難道已從醫生那裏獲悉死產消息,不對,院方哪有他的聯絡方式?帶着紛雜思緒走到臥室門口時,頓然有了解答,這個解答又荒謬得使人理智潰堤。
高大魁梧的他,擺出倒豎着的跪姿,兩腳朝天躺着,通身健碩肌肉盡是滴蠟流淌,肛塞形似蠍子尾巴懸吊,彈跳着被抽打得紅腫的陰莖,自食其力地含住前半截。同場有個陌生女人身穿蕾絲馬甲,兩團巨乳幾乎擠到脖頸,岔開腿坐在男人臀部上,揮舞調教馬鞭,扮演嚴刑逼供的拷問官,自顧自地指交狂摳,蜜汁噴得彼此滿臉都是。
看得兩眼圓睜的龔亮熒,不慎鬆開雙手,捧在掌上的死胎悠揚着四肢墜落。
「噗——」嬰屍摔碎在木紋磚地上,綻放成腐肉四濺的血花。
「老婆,先聽我解釋!你不肯陪我玩這些,」被逮個正着的丈夫連忙起身,肉莖搖個不停還在滴漏前列腺液,與肛塞連珠的鐘擺同步,腿軟得跌撞着,跪倒在妻子跟前求饒道:「我衝動了,以為你又要加班,是我的錯!」
龔亮熒閉口不語,臉色僵硬,低看着男人滑稽的蠢樣子,頃刻間未能反應過來。
非要將屁話全都講完,丈夫才意識到妻子披着病人服,錯愕地伸手摸肚,驚覺腹部的那座小丘已被夷為平地,又不敢往失胎的方向猜想,焦炙得抬頭怒目大罵:「你對我們的孩子做了甚麼,孩子去哪了!」
「認錯的人,要先低頭。」龔亮熒呆若無祀孤魂,逕自轉身,緩步而去。
聽完不解其意的丈夫,彷徨低頭,方知胎兒的殘骸已然碎散在地,當場痛哭狂號,急得徒手拾起肉漿,如捏泥巴般想要黏貼完整。全程待在臥室不敢出來對質的情婦,亦硬着頭皮從門縫探頭,窺見此等情景,突感胃酸直湧喉嚨,猛地彎腰吐出,事關屍血沿着地面坡度沾到男奴莖頭上面了。好樣的,遊子尋根回到發源地。
龔亮熒臨到玄關,瞧着掛在大門的勵志海報,又是肌肉老外自我膨脹地大吼,其情商令人堪憂,配有受虐傾向提倡的老套名言「痛,就是軟弱離開身體的感覺」。請別再不懂裝懂,痛,是逐漸喪失所有感覺,譬如現在——
「啪嗒!」朝着門板磕個響頭,磕得鼻血直流,卻若無其事地拉門離開。
因為沈湎於悲哀也毫無用處,好歹得有表面傷痕,所以龔亮熒前往就近的警署報案,訛稱遭受家庭暴力,以申請人身保護令,禁止丈夫靠近自己的住址及工作場所,為了申請強制離婚作好部署。當她抵達醫院驗傷搜證,抽血檢測能否與屋門上的血型匹配時,居然確診「人類疱疹病毒第五型(HHV-5)」,除非是免疫功能不全的患者,否則沒有顯着病徵,但還是能透過體液接觸、器官移植、母嬰垂直傳播。
先由情婦傳給姦夫,再由姦夫傳給自己,最終由胎盤引起原發性感染造成死胎。
生命裏僅餘的美好毁於旦夕,換來是這險惡的玩意在體內潛伏、增殖,從文字記者到疱疹患者,龔亮熒徹底坐實比髒話更難聽的稱號,愛蟈者所指的毒媒。
ns216.73.216.8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