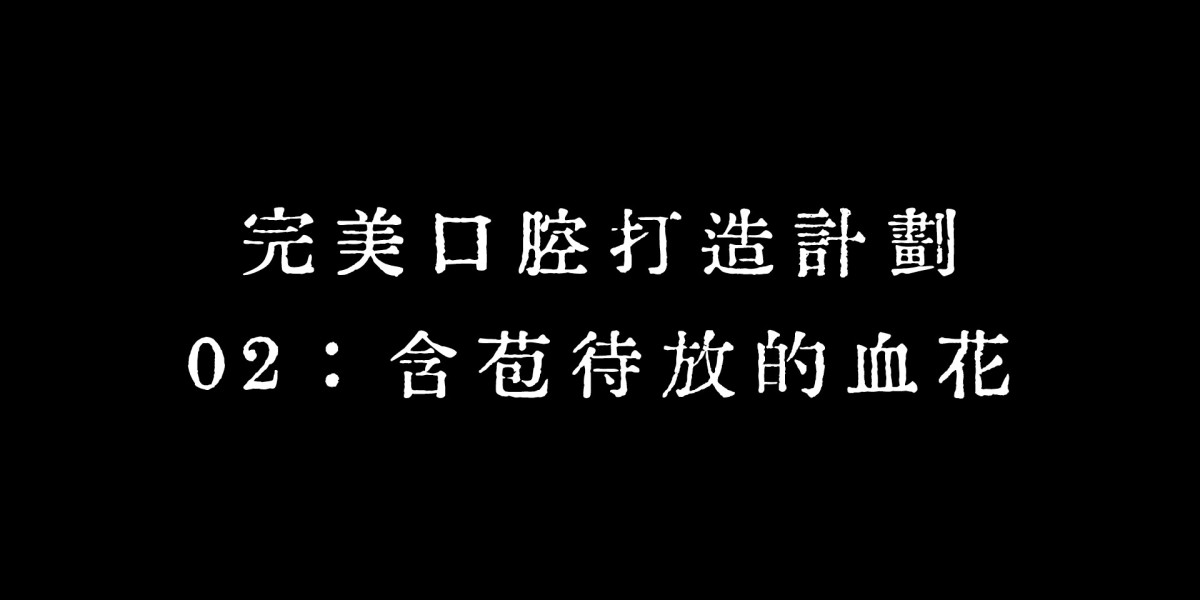
撰稿員的職銜是言過其實了,誰不是把蒐集到的資料輸入到聊天機器人,讓它生成大篇大篇的文字稿?幸好新聞業重視透明度,人工智能的黑箱作業引起違反新聞準則的爭議,龔亮熒才沒有丟了工作,儘管只是易碎瓷碗。
有趣的是,龔亮熒的裝束與親妹的殮衣相似,簡樸西裝套裙,經典黑白配色,表面是傳統意義的記者,實質是懷胎五月的人妻,腹部微隆,正打算在領取有薪侍產假後辭請,改當全職主婦。在此之前,仍舊要回到辦公室上班,坐到工位分隔板前,面朝這幅陰鬱的灰藍色,盯視那個卡頓的彩虹圈,為了打開排版軟體,虛擲分秒。
由蒐集資料到生文潤稿,由生文潤稿到圖文排版,智械革命沒有令打工人的工作量減少,所謂的跨領域整合,就是在人工智能輔助下,讓更少人手包攬以往幾個部門的專業,唯獨失業率在持續急升。
「各位,」總監步至座椅間隔的走道上,拍了拍手喚起注意,「聽好!」
總監名叫盧興邦,是個律己與待人同等嚴格的老頑固,常因小瑕疵而大暴走,部屬們都在背後稱呼他為「勞氣邦」,但也很清楚他是面惡心善,畢竟作為曾榮獲卓越新聞獎的前輩,多少配得上幾分敬仰。當職員在各自的座位起立,或壓下椅背從屏風後探頭,聽候盧總監為這天工作下達指示時,他沒有趕着分配專題,而是率先打點人命攸關的重事,龔若曦的死訊。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台柱在報導落雹時遭到毒手,還要向全城直播。」
盧興邦摘下黑方框眼鏡,直掐眉心,眸裏不由泛起淚光:「坦白講,我真的很生氣。雖然我不總是贊同曦曦的做法,她說要導讀時政大事盤點,我覺得與她形象不對,用體藝和天氣報告來推搪,但現在回想,又很佩服她的進取心,只要定下目標就會提起幹勁去追逐,跟我這種老頭子抗衡,單憑這點就贏得我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曦曦是我們的人。」他抬手擦去淚,戴回眼鏡就是睜眉怒目,誓不向惡勢力低頭。
「亮熒,我明白你有孕在身,交給你來為妹妹寫訃聞,應付得來嗎?」
「哦,都可以。」龔亮熒背手肅立在大老遠,答得異常冷漠。
無論看起來再怎樣無情,人們通常不敢貿然指責死者親屬,甚至會幫忙找藉口,要麼特別堅強,要麼未能從凶訊中反應過來,還是別去折騰這個可憐女子。而且她的性情孤僻,總是獨來獨往,揣摩着自己的想法來反駁自己的想法,既讓她的社論文章常有精闢見解,也造成不好親近的印象。
「那個獵牙人以為能恃雨行凶,在鏡頭前帶走我們的人,拍屁股走了就完事?」盧興邦伸手指向兩名記者,先是老鳥馨姐,再是菜鳥阿魏,「馨姐,你訪問目擊者整合凶殺案的線索,這個頭版我們跟進到底;阿魏,你來接手亮熒台面上的其他項目,原因我想也不用多說了。」
自問對殉職人員有個交待,便即分派當日專案,這頭是川普病逝孝子巴倫赴梵蒂崗,那頭是以軍欲攻阿克薩清真寺重建第三聖殿,再搭個俄中印聯盟散架貿易戰持續,僅是遠在天邊的軼聞,便令獵牙人顯得無足掛齒。
「還有我說過很多遍,不要瞞着我用AI!」盧興邦每天強調,幾乎變成口頭禪。
等到總監回到房間了後,職員們才背地調侃,簡直是反智械大聯盟代言人,應該寫成標語印在恤衫上當制服,請即拋售輝達,別讓大腦萎縮。同事說笑只是想化解壓抑氣氛,忘記顧慮死者親屬的感受,片刻才驚覺失禮,卻見龔亮熒不動聲色地坐下來,掩埋在桌子隔屏後面。
鼠標點開對話介面,無視上司反對,輸入提示詞來輸出悼念詞了。
關於人工智能的黑箱作業有違新聞準則,龔亮熒只覺無聊,憑甚麼肯定碳基比矽基更公正持平,難道人腦不是黑箱嗎?所謂交際就是透過觀察資訊在輸入和輸出的變量,以窺見箇中規律,這是為何有些人容易預測,有些人容易控制,但也只可以間接推論,無法直接證明那些言行背後的動機。
頸椎上頂着黑箱,誰能沒有陰暗面,連品行正直的盧總監亦隻字未提同是受害者的攝影師,還談何公正持平,貴賤分等倒是很明確。倘若真的要遵循內心親筆撰寫奠文,真的要揭開黑箱,龔亮熒定會在開場白寫道——
我多麼希望回到三歲那年,用枕頭把搖籃裏的你悶死。
還記得小時候,你上過兩堂暑期兒童烹飪班,便自告奮勇地準備晚餐,白飯濕得黏糊、紅肉煎成焦炭、青菜沒洗乾淨還有條蟲,爸媽照樣送予掌聲和表揚,那是奉旨洗碗的我不曾有的嘉許。又例如,我在升中呈分試中名列前茅,雀躍地拿着成績單回家給爸媽看,他們只是勉為其難的接受,對我說,也要督促成績不佳的妹妹學習才有用。雖則我擔起了當姊姊的責任,手把手教,但你顧着刷抖音看短片,變相我要代寫作業,顯然你注意到即使欠交功課,挨打受罵的也是我。
這些可不是我討厭你的原因,當你才剛滿八歲,搖頭晃腦地牽着我的小手打圈子,稚氣童聲地懇求我別生氣了,我能不原諒你嗎?你的笑容把我給融化了,連抱怨父母偏疼你的資格也沒有,正如我愛惜你多過愛惜自己。
你若晨曦乍現,我在夜裏微熒,單論名字就把我比下去,而隨着青春期發育,我倆距離再次大幅拉遠。簡而言之,你是個拾遺不報的基因小偷,雙眼皮、翹鼻子、花瓣唇、鵝蛋臉,好東西都遺傳到你身上。我卻是個頰凹顴凸的皮包骨,眼距寬、扁塌鼻、嘴唇薄、菱方臉,癟得連鑽入枯柴堆也毫無違和感。別說相由心生,姊妹爭美太過心胸狹窄,你長着字母表第五位的罩杯尺寸,我又只能屈居第二。
我瞭解到自己是個善妒的人,與其自哀自憐,不如互助互勉,向你請教如何梳髮畫妝,乃至時下熱門韓劇,就當是為這些年的差別待遇索要補償。我倆關係因此變得親近起來,你還四處張揚家裏有個品行兼優、務實精明的親姊姊,搞得我莫名其妙當上學校風頭躉,交了個比我小兩歲、名為湯澤霖的體育生男朋友。
然而在我升讀大學前的空檔年,妹妹,你實在錯得太離譜了。
當時處於社會動蕩期,事涉港臺兩地的跨境凶案引起修例風波,逾百萬市民上街遊行,當局卻置若罔聞,並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二讀審議,連隨演變成警民衝突。催淚硝煙四起,橡膠子彈橫飛,推着鐵馬護欄在大馬路上行進,其鋼材振動令人手指麻痺,撂掉破傘,擲出磚塊,刺鼻灼眼的涕零沿着生理鹽水滑過臉龐,比出生以來流過的淚加起來尚要多。
因為我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大是大非面前理應要放下小情小愛,所以我沒有急於拆穿男友,哪怕我早已察覺你們勾搭上了。你非要在抗爭現場鬧小孩脾氣不可,玩起捨命留守的戲碼,遠談不上行公義,只是逼使澤霖在你和我之間作選擇,還說真的在乎你的話,就該中途折返護送你離開。
那夜在理工大學,澤霖為救走我家養出來的白痴,被警方拘捕,經審訊裁定暴動罪成,被判囚五年零三個月。毋須美化義士的人格品質,他並非合格男友,我親手把他送給你又何妨,豈料失戀的我連恨也恨不起來,他不該遭這種罪。
事隔三年,輪到你面對升學壓力了,文憑試成績差又不是天塌的大事,天賦各有不同而已,在我看來,這些學歷證明書過剩得形同廢紙。我提議攻讀副學士銜接上去,起碼能獲政府資助,別想着報讀費用高昂的自資學士課程,父母積蓄才不到幾十萬,讓他們手頭寬餘些,我們扶養兩老也不用太吃緊。奈何你不甘比同齡人遲起步,說要當個與閨密們齊上齊落的大學生,天知道那是甚麼鬼,只知爸媽不惜省吃儉用繳交學費,同年九月,你毫無自覺地重遊理工上課。
更遑論疫情肆虐,接種疫苗反倒讓父母健康每況愈下,還罹患肺癌,或許我不該過度臆測,老媽有吸煙習慣,老爸是長期曝露於有害塵埃的建築工人。重點是,標靶藥物的價錢每月約為五至八萬,療程長度須視乎情況而定,有的甚至可達二十八個月,多虧那個服務同輩攀比的自資學士學位,他們都活不過四個月。
靈堂祭壇立有父母的黑白照,我倆姊妹呆在停柩室內瞻仰遺容,無暇招呼那群遠房親戚,忙於籌備喪禮的我未敢宣洩情緒,否則誰來辦理正事?但望着你跪在兩副棺材面前,哭得梨花帶雨,無助好比丟失了奶嘴的嬰兒,害得站在你身旁的我亦暗自心碎。
「你真的好可怕,」你抬起頭盯着我,抽噎道:「怎麼能不掉半滴淚?」
謝了,這下我更加哭不出來,你佔盡便宜還要反過來指責我,因為我不願呼天搶地打悲情牌,眼淚沒那麼廉價,所以活該忍受你的蔑視嗎?對了,當日我們在靈堂上重遇湯澤霖,面貌比以往憔悴,據聞是行為良好提早獲釋,出獄不久便前來致哀,你卻無法從人群中認出他。
雖然你在事後向我道歉,說自己太過悲傷才遷怒於人,想要繼續當好姊妹,但縱使我強裝大方地答應了,也試着再三原諒你,就是未能拔去扎在心上的刺。
直至出社會,持有廣播牌照的新聞媒體屈指可數,我倆無意間當了同事,你無非是亂投上百封履歷,還好意思告訴我這叫姊妹緣深。試用期屆滿,你因長得漂亮而調任成為新聞主播,正是我想調往的崗位來着,在幕前亮相,乘搭着無線電波穿房過屋,好讓外界聽見自己的聲音,你連這個都要跟我搶。到現在,人們顧念你不幸身故所給予的關注,依然遠高於正在孕育生命的我。
當然,諸般私人恩怨又豈能登報?逝者已矣,無謂鞭屍。
「美人殞逝淚沾巾,哀思無垠意難禁。」龔亮熒為訃聞潤稿,並在結尾寫道。
鑒於龔若曦死於謀殺,須解剖屍體確定死因,調查凶徒的犯罪手法以供心理側寫,絕不得豁免剖驗。正好龔亮熒沒有打算申請豁免,懷有身孕卻毫不避諱,更提出旁觀剖驗過程,走過狹長空蕩的醫院走廊,踏進電梯,按鍵關門。
先經過沖身室消毒,再穿上防護衣身及外科口罩,才可由護工帶領前往驗屍間。有別於陰森冰涼的普遍聯想,這裏寬敝明亮,室溫偏低,卻不至於讓人呼出白霧,除了嗅到冷藏肉解凍的腥腐之外,算是挺不錯的環境。
龔亮熒步往驗屍間中央,俯視着這具曾以姊妹相稱的女屍,平躺在不銹鋼解剖台上,正俏美嫻靜地裸睡,凡是長得醜的看了都得飲恨自盡,連屍斑遍體也豐美撩人。
忽聞側近有個音痴在大展歌喉,龔亮熒循聲看去,瞧見巴基斯坦裔年輕女法醫的側影,她戴着紫丁香色耳機,哼唱鏈鋸人最終季主題曲,而且還是網民改詞的廣東話版。這年頭普通話滿大街,幾乎能不理音準盲目誇獎唱得真好,邊跟着節奏點頭律動,邊整列骨鎚和骨鋸等解剖器械,完全陶醉在自己的世界裏。
「咳咳。」龔亮熒不苟言笑地站着,假咳示意提醒。
女法醫瑪麗安聞聲回頭,瞪着濃眉大眼,露出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
這個居港巴裔哈日的動畫宅,工作表現倒是不失專業,拿出透明平板電腦掰至彎曲,替遺體正側面拍攝環景照片,上載至量子雲,藉由圖稿生成立體模型以便深入分析。轉而握起了剪子與刮刀,使用傳統方式採取微物跡證,總有些行當尚未被人工智能取代,或因國際局勢而令相關技術不在本地普及,瑪麗安不曾因此質疑自身的價值,懷着謙遜待人處事即可,譬如向行外人解說蒐證發現。
首先,死者指甲縫中藏有熟革纖維,估計是掙扎所留下,可惜凶手穿着長袖連體皮衣,故未能搜到皮屑或毛髮;然後,繩索勒痕由胸口交錯到肚腹,由手腕延續至足踝,只有背部沒有捆縛紋路,言明生前曾被綁在高背椅上;接着,口腔殘留牙刷硬毛,牙肉遭到鈍刀挫傷,到底是何種變態要在拔掉牙齒前,徒費工夫為受害者剔除牙垢?
雖則屍體沒有明顯致命傷,擺明是投毒身亡,但在剪下頭髮以探測曾否攝入重金屬後,該到最後的解剖環節,從而摘取器官與體液進行毒物檢驗,辨識貨源以追蹤凶手過往行蹤。
「你會不會出去暫避,我記得有句話,動胎氣?廣東人是這樣說的。」
「家裏不介意你當法醫嗎?伊斯蘭家庭似乎都管得很嚴。」龔亮熒言辭犀利。
「哈哈,阿拉知道我在為民申冤。」瑪麗安連心腸也較為柔軟。
「恭喜你有自己的抱負和信仰,請繼續。」龔亮熒無意閑聊,忽悠過去。
姑且撇開宗教不談,就算是無神論,誰會大着肚子想要旁觀解剖?這個龔亮熒竟親自來訪,帶着跟監工敦促似的壓迫感,令碼麗安好不自在,還是剖驗屍體要比揣度人心簡單得多。
先以手術刀由兩側鎖骨割向上胸,再垂直割向肚臍下三寸,使切口呈大丫字型,便徒手伸進皮肉裏往外掰開,撥開淡黃色的脂肪免得干擾視線,用鋸子把肋骨逐根移除。整個軀幹登時淪為洞見肺腑、肝腸畢露的敞蓬車,見慣不怪的碼麗安照常抽血備用,逐塊逐塊器臟切取,放到電子磅上秤量輕重。
反觀龔亮熒作為死者親屬,瞄了眼工作台上的心肝脾肺腎,轉回來看向那副空殼,既不帶愁容,亦不覺震驚,還反常地露出含蓄的甜笑。原來是寬恕兩字被過度高估了,姊姊真正需要的,不過就是將妹妹剝皮拆骨。
偏在她人生首次感到幸運的時刻,孕肚暴發抽痛,子宮裏面恰似灌了鉛塊,自內而外撕裂下墮,轉瞬間把意志和力氣給榨盡,失足跪倒在地,卻因自小屢受責打而本能地咬牙吞聲:「嘖。」
「誒?」瑪麗安捏在指間的膽囊不慎滑落,照字面意思就是嚇破膽,正想上前攙扶,怎奈滿手肉毒桿菌,唯有用肩膀推開門出去尋求協求。
ns216.73.216.238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