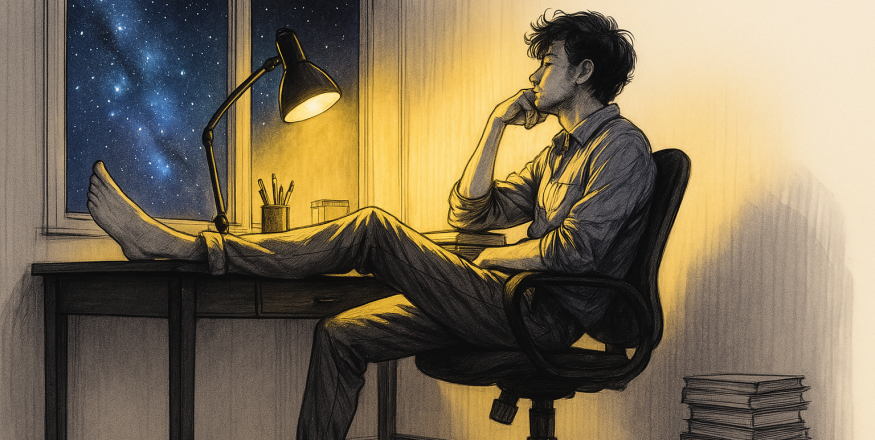x
x
從1999年7月的諾查丹瑪斯預言,到2012年瑪雅曆法的終結,再到近期備受討論的2025年7月5日,龍樹諒預言的大地震與災劫,世界末日的傳言像季節般輪迴不止。每隔數年,總有人聲稱末日將至,有人擔憂、有人冷笑、有人準備地下碉堡,也有人買了最後一張機票去旅行。這些預言最終全都落空,世界照常運轉,但那種「終結」的念頭,卻從未從人類心中消失。
為什麼我們總在等一場終結?我們是否真的渴望世界毀滅?
答案,也許比表面想像的更複雜。
首先,世界末日的預言,反映的是人類面對「無法掌控未來」的焦慮。當災難頻仍、氣候變遷、政治混亂、科技越過理解的界線,人們自然產生一種末日感,將現實的不安投射成一個具體的終點。1999年,人們對電腦千禧蟲的恐慌;2012年,對文明崩潰與自然報復的揣測;2025年,人們對龍樹諒所說地震與滅世災難的集體凝視——這些預言之所以引人共鳴,並非因為它們必然實現,而是因為它們貼合了人類對未來的恐懼與無力。
但這還不是全部。
世界末日也是一種潛在的「解脫」。當生活苦悶無望、當壓力重重、當人際冷漠或制度失控,對某些人而言,「一切歸零」竟有種詭異的吸引力。它讓人暫時忘卻責任、債務、壓力與失敗,彷彿末日一到,一切罪與痛都可以毀於無形。那不是對毀滅的渴望,而是對現實無能為力後的求生本能。
更深層地說,人類之所以幻想末日,也因為我們潛藏著對「重生」的渴望。許多預言裡的毀滅其實不是句點,而是逗號:洪水過後有方舟,火焰過後有新世界。人們在想像世界崩壞的同時,也偷偷許願——若能重新來過,也許就能擺脫一切錯誤、遺憾與束縛,走上更好的路。
我們從不真正想死,只是不想再這樣活著。
所以,人類不是渴望世界毀滅,而是渴望某種「意義上的結束」——某段歷史的終結、某種錯誤的終結、某些壓迫的終結。末日預言,也許不該視為荒謬迷信,而是一種集體潛意識的映射,是我們對秩序混亂的反抗、對現實無力的回應、對重生希望的寄託。
世界末日從未來到。但它一直活在我們心裡,期待著滅世降臨。
ns216.73.216.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