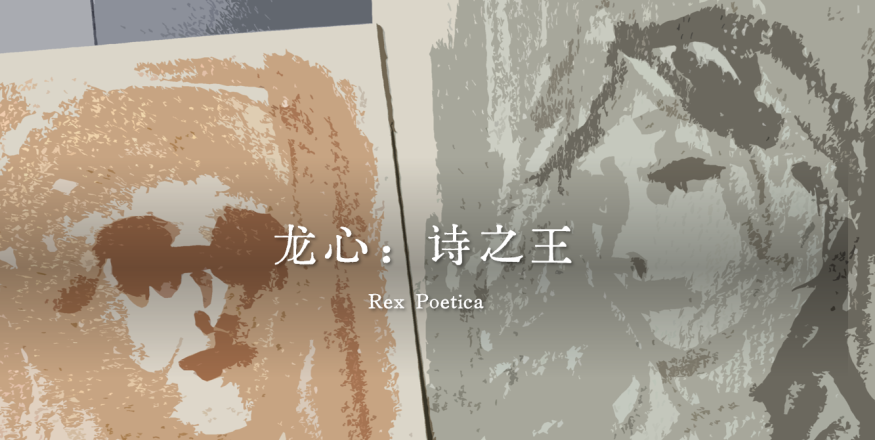Réconciliation(和解)
E曾经是海英慈的网友——标明此事是必要的,因网友一词本身有足够的内涵(la connotation):交友的原因可能起始于兴趣,交友的模式可能单一于互发消息。交友双方可能很难避免不对彼此有偏颇而完全不切其作为一个生活在物质界生物体(un organisme)的理解,而在彼此眼中都化为某种嵌化在硅心电波中的意识,一种无处不在的当代赛博格(cyborg),而、因此同被冠名为“对方”的虚空寄托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其质地效果从纯粹的滑稽可笑到严肃的沉思冥想不等。
对一个网友的发言产生强烈的,几是瞬发而无法抑制的剧烈反应(愤怒,疑惑,悲伤,迷茫,etc……),尽管从现象上,海英慈完全可以理解其被称之为可笑的原因,亦不是不能反身性地作为一个外部的评论家(critic)去描述和解决它,但对于一个参与者(participant)而言,面见这社交媒体的主页,她心中只有难以言喻的耻辱,惊愕,愤怒,和些许的迷茫。
万教授仍在讲课,海英慈却既未聆听,也未看自己的书,而全将注意力放在了E的社交主页上——不是说,这页面上写了什么引起她愤世嫉俗的观点,或是说了什么和海英慈有关的话题——她越翻,眉头则越是蹙起。
恰恰相反:这主页上什么也没写。
E这个在本国最主流的社交网站上,大约有五百个关注者的账号,对海英慈来说可谓是毫无内容。若被迫与其进行单向社交(one-way socialization),已使海英慈倍感屈辱(其中诚然有很长的背景故事),于其中一无所获,则使她不得不感到焦躁和迷茫了。E 的更新频率很低,一周的平均发布量约在十条左右,其中许多是转发,内里不乏素材积累和宣传模范人物的新闻,而剩下的一两条,则最可能是她观看文艺作品的感想和听歌后忽然爆发的情思。E自己也是个文学创作者,所以其中也一二有她对未来作品的构思发想——但对于“有”的这个状态,海英慈的心不是那么确定。
“……太**少了(so Damn FEW)。”她忍不住扶额,又在指缝里,看见E最近的一条纯原创性的动态,写的是:
“……这漫画毫无疑问是国漫第一。”
她把眼睛闭上了。
shame(丢人)。这是海英慈的第一想法,面上浮现似流泪圣母像(Weeping Madonna)上无语望苍天的神情。她无法抑制这种感受。
海英慈知道E所说的那个漫画,连载时间已达九年,在亚文化和图像传播圈里颇有名气——却没有让她觉得值得去看的价值。她首先并不热爱看漫画,第二,就她打开这本漫画的经历而言,她不喜欢作者描绘第一个出场女性角色的感觉:这名少年女性身穿过膝长裙,手托行李箱,另一只手握闪寒光的匕首,中分长发,面部描绘简单,没有什么殊胜之处——但她直觉可感,这个作者对女性的精神性没有什么了解和偏重,而她对此类作品也无兴趣。经过了七八页关于“盗墓”事件的开端,第一个男性角色在厕所里小解的片头将她请了出去。
So vulgar(太低俗了)——并且毫无必要。她捂住脸,沉默下滑E的社交页面,被迫反复品味她已发表的动态。继此条评论漫画,续是先前的一处文评。
“去极乐净土吧!”
甫见“阿弥陀佛(Bouddha Amitābha)”,“花开见佛(Voir le Bouddha lorsque la fleur s’épanouit)”,“极乐净土(Terre Pure de la Béatitude Suprême)”,“业缘(Affinité karmique)”等词,海英慈的心率便是显著加快。她不由开始拨弄自己前额所剩无几的刘海,耐着涌起的反胃感将那文段再读了一遍。
E所评此书,盖是一十年前的网络文学,海英慈不曾读过,不过就她简略翻阅百科,再结合E的描述,约知这恐怕是一个犯罪分子和警察之间的耽美文学,最终那警察可能开枪杀了罪犯,故而“正义”与“私情”难两全了。
“警官,你的当务之急是为他念阿弥陀佛圣号,(他若)留在轮回中只能直下地狱了”——此句可知,其中一男主角应犯了害人杀生之罪。
“去阿弥陀极乐净土便是久远后才能花开见佛,但罪孽得洗涤后,你们二人一定能再度重逢。开枪没什么值得难受的,一定认识到,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海英慈笑了——弧度极深,忍俊不禁。她笑了好一会,脑海中闪现数年间她和E的对话,最终摇头。
“我根本和这个人不熟识,我们两人,直到分开,谁也没理解谁,而她——”她想:“恐现在也不理解我。一点也不。”
她又翻回最上的,打着一个特殊Tag的动态:那Tag的名字叫“忏龙经”,是E特意为她取的,若E发了和海英慈相关的动态,一定归类在里面。
海英慈其实挺喜欢这个名字,但此事就仿佛她和E关系的一个写照——在这段几全是本能性反感的关系里,任何一丝对彼此的喜爱,恐都会带来深重的困惑,和最终,自反感进发而生的仇恨,因它使人去追问那问题:
为何人不能互相理解 ?
海英慈最后看了一眼那条祝她“生日快乐”的动态,关闭页面,打开写作软件。
她开始给E写一段回复——在两人六个月没有说话后。
8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Vmr8nOv3bN
“我们不再是朋友了, 但恩怨也已了结,祝你在你自己的道路上,一切顺利。”
11:35分,第二节大课结束,海英慈已复回去,重新批阅她自己的作品,此时正收书准备外出。她对自己作品最后的成效实际是既自信,又有些忐忑,大体上而言,写作者在忘记自己所写的具体后再回去阅读会有更客观有趣的阅读体验,但海英慈因好奇,写完就迅速打印,不到三天就开始重读了。对《血圣女》,至五十万字的时候,其质量海英慈认为全无问题,但在五十万字后,到了一月,海英慈开始犯严重胃痛时,成品则是她难以预先判知的了,至一月到四月,后五十万字中,她的写作体感渐渐同前期经验完全不同,至于到了倒数第三卷时,她竟生出了丝茫然无措感。
不过现在倒是清晰了。她关上书,爱惜而珍重地抚摸它贴着木浆纸的封面:写完最后一章节时,尚是当天上午,她疲倦不堪,精神却亢奋,当时便整理格式,导出PDF交给印厂了,不想调整时标题写错,只好用纸糊上。
“……这是场清晰,完整的梦的破裂。非常完整,诚恳,详实……并且很美。”她对自己想:“很好的作品。比我想象中还要好,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
她起身,边想此事,边同其余所有人一起,妥善而平常地整理随身物品,离开教室。海英慈环视教室里学生的面容神态,听见四处的声音,见有结伴欢笑的,也有上台前于万教授交流学术问题的,脑海中似有个声音,平和地默念,描述他们的行动:那结伴欢笑的女学生讨论的是周末的安排,或去做志愿活动,或去踏青,或有作业,台上,万教授身边的学生则问她关于某个理论运用在论文上的可能性,又,也可能是厘清先前上课没有完全明白的某个专有名词——所有这一切,对海英慈而言都没有任何吸引力,甚至,在她心里,她全然认为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她对所有纯粹的自我上进活动和平凡温馨的欢声笑语都似保有某种先天的敌意(Hostilité),而此倾向,先前,并非不曾给予她特殊的烦恼:
学业 (Performance académique), 志愿 (Projet de bénévolat), 实习 (Stage), 工作 (Travail), 社交 (Relations sociales), 微笑 (Sourire), 礼仪 (Étiquette),没有任何事是海英慈乐意做的。整整二十四年来,凡涉及到其中的任意一项,海英慈都在忍耐和伪装。
她现在也依然在做这件事。海英慈应和常桦一起离开——她正靠在常桦旁边的桌边,看着她与一个巴拿马留学生交谈:这个留学生是个华裔,却不会说中文,不大明白课程presentation的要求,常桦和她组队,正在和她商量主题选择。她可听见常桦说英文的声音,情绪饱满,温柔而热情——如她本人般,听此嗓音,海英慈也露出笑容,作出副友好而好奇的模样在旁聆听——尽管这多余的课程中多余的任务本身令她全无兴趣,唯是常桦和留学生Lalia的交流本身,让她记在脑海中。如此事件(Événement),呈现在她眼前,才让她感某种“感官”的激活,足使其作为一瞬间,变化而凝固的抽象符号(symbole)留在她心中——否则,一切对海英慈来说,如在先前数十年中,不过是一架不断运动的处理机器和种种混杂了厌恶,愤怒,鄙夷的情感的浓浆(plasme)。面见常桦和Lalia的对话,海英慈感到一种美的原材,可在将来,为她所加工,附以种种装饰,生以联系,彻底嵌入她所向往的,那关于美的整体中——那亦可,被称为美的“库”,美的“躯体”,一个抽象的,但从局部到整体,无不透露出和谐和美的事物。
那就是海英慈唯一感兴趣的事。凡她在过去忍受的日程和社会安排,主动或被动寻求的不快和进行的学习,不过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因此,她也足在对社会生活全不感兴趣的情况下,勉强与此相安无事。
尽管那不是没有巨大的烦闷和不适。但一切——都已是过去。海英慈面带微笑,环视教室,感思维机器轻松而顺畅地运转——因那用于模拟情绪和景观的区域已在平缓如柔板(Adagio)的环响中,建构已毕,其在自发的存在中,无需她,再以双倍的出力,维持内外双方,那关于美的追求,和迎合社会机构的行为的共时进行。现在只剩下——一些最基本的伪装和,无视。
而,这相比于前二十四年的艰苦,简直是——
太爽了(So damn fine)。
“thank you so much Lalia, we discuss later in Wechat group, will that do ? ”
“of course……”
海英慈不得不将手放在嘴唇边,来掩盖她过于明显的笑容。但这就是现状:她如今每天可谓是笑容满面,先前给E的回复,哪怕那祝福本身仍令她有一瞬的不快——在这巨大的闲适和轻松的对比下,也依然轻而易举地使其变作了一和解和感激的礼貌送信。
无论她先前和E有怎样的不快,她的新生活都足以让它过去。
E曾经误会她的为人?
没关系。所有人都会犯错误。她相信E没有恶意。
E曾经无视过她的作品?
没关系。人各有好。
“英慈,我们走吧?”
海英慈只要能够继续追求她心中的“美”,对于些细节上的问题,皆可视若无睹。
“——噢,好。走吧。懿文该在等我们了吧?”
她收回先前夸张的笑容,换上了跟舍友们相处时孩子气,讨好而友善的神情。这倒算不上很难,因海英慈认为室友们各有可爱,诚为一“美”,她不曾觉得特别不快,只要社交时间不长,不成负担。
“我们在楼下等你。”海英慈打字通知林懿文。教学楼外的小花园中,有一处繁盛的猬实,色白,云丛而下,垂于一长椅上,林道汇聚,如穿行之门。此花乃本土花种,属忍冬科,据说唯一外国植物学家在南方一省份的深山中发现,引为园林植物,后亦成为他本人的最爱。
有品。海英慈判断。
“你们已下来啦,我还在楼上等你们呢……”
林懿文从门内奔出;这个周末愿为自己的社会关系奔波的年轻女子透露着朴实的生活气息,海英慈从中闻到一种温和的木香,这意味着她暂不需要设防——也不需要在安排社会出行活动时,担忧细节礼仪上的无意冒犯,一切——都如这有猫群穿行,玉兰簇拥的花园般,在它最温和而简单的形式中。她几乎像睡着般轻松,尽管她已然苏醒。
“我觉得门口不容易出错,就选在这儿回合了。辛苦你等了这么久,懿文,”海英慈微笑道:“桦桦在和她的搭档交流。她是个巴拿马留学生,不太熟悉这节课的任务。”
“巴拿马人?”
林懿文果然很有兴趣。三人便向校门口走,边讲述和这留学生有关的趣事,边叫了车。阳光很好,海英慈的黑衣让她有些热;但实在是没什么可抱怨的,只让她生了丝担忧:这生活太轻松,让她不禁询问,何时会结束。
8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SniG1D737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