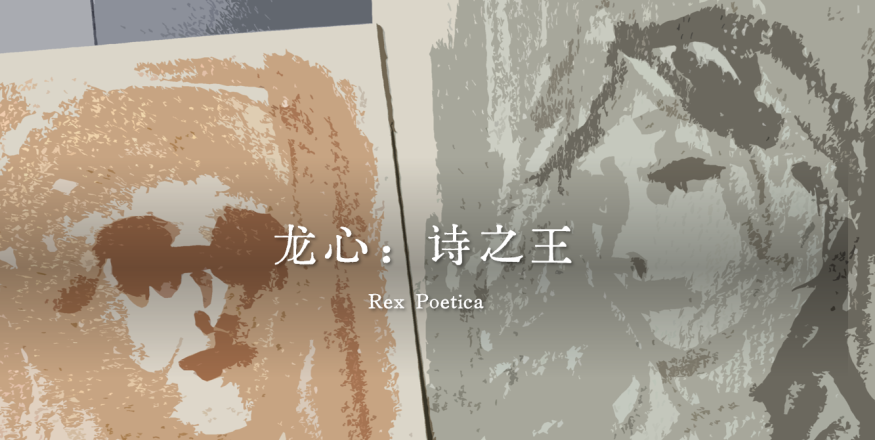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理性的毁灭》)
“……懿文,来看看这个句子。”大约四月十五日时,海英慈将先前首次“二进宫”式从图书馆背完的书看完了,最终认为,对她未来写作最有益的,就是手上这本由卢卡奇写的《理性的毁灭》;1988年版本,当年只要八块钱。
“嗯,什么句子?”
林懿文回头。宿舍中,若勉强可说在这所文科大学共有的领域(语言,哲学,外交,文学,etc)里碰到了什么海英慈感兴趣的观点,她一般会找林懿文。三个室友中,尽管最经常叹息学术困难的是林懿文,海英慈却可看出她才是三个室友中最习惯,也最喜欢进行纯粹理性上思考的人。常桦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基于她的感性——常馨比起思考,对行动更有兴趣,一来二去下,海英慈和林懿文之间倒经常分享些观点,作茶余饭后的消解了。
“这本书……简单来说是一个叫做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某类思潮中所有名家的批判。”海英慈在念这段话前介绍了番,因知林懿文对现代哲学的名字了解不多,稍介绍番,防止影响捉重点:
“……在写完《审美特征》之后,卢卡奇决心为马克思主义撰写一部伦理学著作。其三卷本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是他以抱病之躯奋力疾书的绝笔,但终于没能完成。卢卡奇于1971年6月4日逝世。”
她念完了句子,却自己也感没能传达她想分享的观点,干脆将事提出来说了:“‘抱病之躯奋力疾书’这个描述让我……深有共鸣,并且很感慨。这本书不是他的后期作品,但无疑,他一辈子都在不停地写书,思考,而且我觉得最独特,最了不起的是,他批判的都是些鼎鼎有名的哲学家——丝毫没受这些人的名气,拥趸和成千上万的冗杂语句的影响,根本彻底,毫不留情:谢林,叔本华,基尔克戈尔,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马克思.韦伯——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些人——对不起,有些长了——但言而总之,我感慨的原因是——他的批评其实是对当代的互联网舆论环境很必要的。在各个社交平台,尼采和叔本华的观点都在以娱乐化的形式出现,同样普遍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在其中最重要——不,我认为可能是最戏剧性,最连贯的是——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做的事,其实是在完善马克思主义,并将这些哲学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显示出来。”
“连贯?”林懿文听着,对这个词提出了疑问。海英慈微蹙眉,最后还是决定,稍解释番: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中所引起的历史运动和社会变化而言——你可以想象成一个故事的连贯。他没能完成的这本书几乎存在某种戏剧性和命运性,再听听这个句子。”
她念道:“
“……卢卡奇所以在垂暮之年仍以完成一部伦理学著作为自己的使命,是基于他的一个认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崇高意愿在于关心人,关心人的价值、尊严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命运和前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已在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指明了解决的基本原则,只是生前没来得及深入系统地阐述。而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及时理解和发展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许多资产阶级代育人就要乘机出来钻空子。”
林懿文皱着眉,她望着海英慈,而这个表情通常来说代表,她没有明白海英慈想要提及的方向,而,对海英慈来说,这种愿意聆听她的倾向,已经让她很感激和高兴了。
“——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是没有伦理学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海英慈因此解释:“我们这个社会大部分的问题,是古来的民族潜意识和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机械唯物辩证法所引起的。因为一切都是唯物的,机械,以物质为基础,经济状况决定上层建筑的,导致在这个国家治理和社会唯物体系中,所有的价值批判,其实都仍然是基于物质,而使所有精神上的问题没有任何法律,哲学的根基,甚至其实成了异端,这就是为什么教育上存在如此多的军事化学校,各类处于灰色地带的虐待行为层出不穷。”
“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络上典型的话术,本质都是基于这种系统化的‘唯物主义思想’——当我们辩论性工作者,彩礼,动物解放,无节制的技术创新时,许多人会回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亦即,在没有出现技术和物质层面的解决方案之前,人类对种种社会现象没有任何的发自精神的对处能力。”
“噢!”林懿文感慨。倒不是海英慈说得有多好——她本来就不大善于做这种基于专有名词的总结,文段七零八落,但林懿文起码明白了她在说什么,这让海英慈很高兴,她继续说了下去:
“而这位有人文关怀的倾向,旗帜鲜明地反对消极与悲观,不事社会改良哲学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死在了他能完成这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著作之前。换句话说,他本来应该能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已经为此做了一生的准备,但他没能完成。”
“那很不幸。”林懿文说。海英慈的眼睛却亮了,她摇头道:“不。如果只有这一层,还不足以引起我强烈的兴趣,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其实他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这部著作的。听听这本书的名字《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社会存在的本体,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肯定应该是物质的,它的精神至多以神经科学的方式存在——但很显然,他若继续探索,就会走到这条道路的终点——发现他和他反对的这些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们走到一块。”
“——他会发现人本质的存在是精神的,这就是他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原因。”
“人的本质存在是精神的么?”林懿文质疑,海英慈摇了摇头:“这一点,没人可以用任何逻辑链去证明。就放在这本书的历史框架里说罢:无论是谢林,叔本华,尼采还是基尔克戈尔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高尚的精神存在’,他们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的历史发展恐会消除这种高尚的精神,因此站在了保守主义派系内,最后为法西斯,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歪曲的邪术提供了根据——因为实在是没人能说,高尚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任何人都可以标榜为高尚的,因此相反,基于物质的,理性的,科学辩证和社会物质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之下,反而正常些了,但这种正常其实只是相对的。整个历史过程,既没有证明高尚的精神不存在,也没有证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存在的理解就是对的,它一定具有社会改良的本质机理,在整个过程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有什么高尚的事物,甚至,还尚且不够完美,确实已是消失了。”
海英慈顿了顿,再次总结:“这本书并不是在哲学层面上让我觉得有趣——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本身,其实由于文风和问题框架之故,很难有意思。它本质上是对人类精神现象的探讨,但不同于神学,需要借助科学基础,又不同于心理学,无法借助实验,位置尴尬,文中无用信息极多——这本书第一起到了总结某派误导性特别强,同时对现代思想仍有影响的哲学体系的效果,第二,在现实层面上,卢卡奇的这本书与那一流派思想恰好相反,以错误的体系,在做正确的事——那边则是以相对正确的方向,做完全错误的事了。”
她笑笑:“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充满了张力,也很现实,给了我很多灵感。”
“你真的从什么地方都能看出灵感来。”林懿文回答,露出了个有点忧伤的表情:“但这样说,感觉哲学好没意义,又得不出什么正确的道理。”
“我不会说‘过程就是意义’,但起码,我觉得像卢卡奇那样,就挺有意义的。”海英慈说:“说出来的话,知道的信息,都没有一颗真正关心社会苦难的心重要。卢卡奇本是银行家的孩子,相反,那些‘保皇党’中倒有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后代——物质决定论如何解释呢?我的意思是,根本上,一个人的心念,一个人的感受,有时才会造成最根本的变化,像这本书说的——”
她拿出另一本书,是莱恩的《分裂的自我》,表情较柔和:“‘重要的是去理解人,有些人看似疯狂,其实正常,有些人满嘴的理智和科学,其实比谁都危险’。他也说,‘时光流逝,我徒增年龄,但今天的我,更老,也更年轻’。”
“蛮文学的。”林懿文评价。
海英慈笑了:“嗯,有时比起逻辑论述,文学作品更能显示这一切的意义啊,我可深有体会。”
8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ts1mLDkw66
这本书对她来说恰到好处地出现——还因为,卢卡奇和生命哲学流派的冲突,也展现了她和E冲突的始末。
和林懿文交谈后,海英慈出门还书。原本她同室友说,起码两个月不动笔写任何东西,修养身体,结果休息不到七天,已经坐立难安,因下一部作品,不是纯粹的虚构文学,而含着她的自传性质。这个构思是两月前偶然决定好的,以来就让她既喜悦又忐忑:通过某一个特殊的设定,她便解除了所谓High-fantasy中包含的逃避主义:使这个世界与现实全然分离,让它显得如异界般完整,梦幻仿佛自有生命固然似是“奇幻”作品的生命来源——和商业模式,大体来说只要这样,人才能于其中放逐自我,沉迷于新奇的探索欲——但这本来就不是她写作的缘由。毋宁说,海英慈更苦恼于她无法兼顾“地标风景类完全象征域(The Complete Mapping of Landscape Symbols)”以及现实批判:《龙心》的计划和初稿开始于她尚且没有对这个世界完全解读能力和方向的时候,而它的地标特征,那些黑海,白山和火原,对她来说又有完全的,命定般的美学吸引力——她并不后悔,也不犹豫,选取这个地理背景作为她阐释自己思想与所感核心的领域——但如今,通过这一个设定,她不仅可以获得那些在她思想冲突最激烈时取得的美学符号,同时可以借助“模拟”的事实,将这个美学场景中与现实语境结合,使其中的领悟和含义,流通(Imported)至现实。
8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cRkJY0V6p
“看——那儿有三个工人,在桃花树下睡觉。”
一日,海英慈与常桦——这个同属外国文学专业的室友在课后回到寝室,她向她指出那一场景:修理储水塔的工人,两男一女,睡在靠墙的麻袋上,四壁阴凉,远处草坪乃是城市规划中的齐整,行人穿着入时,皆是都市脑力工作者打扮,唯这处在沙土凌乱中躺着这三个皮肤粗糙,穿着宽松而赤足的工人,疲倦而又闲适,周遭,花树怒放,竟如咫尺之遥却存在一个正搭建的全新界域。在那儿,女人和男人的边界似不再分明了——由文字和逻辑搭建的精神领域褪去,残余是最纯粹的劳作与再生机构。
她再度想到她时时思索的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这情景很适合记录……象征着一种对于我们这个群体,这个社会来说被忽略却长存的冲突,而发生在一个如此奇异美妙的场景中。”海英慈说:“她们睡着的样子如此恬静,我们无从知道她们的想法。也许她们没有痛苦——这些女工人和男工人几乎没有体格上的差别,虽然这仍然很有可能是一对夫妻——她们寻到的睡觉地点像某种本能,我很怀疑如果是其余的社会群体,能否寻到这样一个恰如其分的地方,这样安静,像和这环境融为一体。”
她一连说了许多,常桦很惊讶。
“我甚至没发现这里有人。”她说:“艺术家确实有不大一样的目光……”
8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qEvYqZjSs
是的——书,文字体系不再是她唯一需要也可以撕裂的素材——生活本身,藉由她一部作品的旋转(Rotation)和位移(Displacement),已变为了无处不在可转化,也必须被转化和呈现的素材。她的身心获得了自由和极大的解放,乃至她对开始下一部的写作跃跃欲试。
这是她发出那实现她曾感绝望——不可实现愿望的第一个基础——虚幻将以此联通现实。
海英慈将书依次推入还书机器,再次望向那书揭示了矛盾本身的标题:理性的毁灭。
不,理性只是个再简单不过的工具,不是理性的毁灭,让文明凋亡——而恰恰是对那更高的,凌驾在理性之上的源头的盲目,使理性的载动无用了;使其变成苦痛而损耗的机器。难道基尔克戈尔没有感受到那精神的大源并试图将其描述,或,尼采没有正确地感受到大部分民众的麻木和根本上的机械性?——但他们的选择错了——不是理性错了,而是在那大源前怯弱,害怕去实现它要经历的千难万险。
8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yVaDLCTJNu
E: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不圆满过。
——那些罪恶呢?那些显而易见的罪恶和罪人呢?
E:他们只是被百劫以来的浊恶所污染,仍有本自俱足,清净自在的真性。
——那这些浊恶又是从哪儿来的?
E:我们无法回答。我和你都无法回答。
8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oUXBsH7RQ
看这本书讲述叔本华的章节时,她想到了E。不是哪一句具体的段落,而是那些跃迁而彼此成网的词语:“永恒不变的自然界 ”“……与他同在”“无法改变,也无需改变”“禁欲主义的美学化”——不,E没有叔本华这么过分。
她只是想,也许E和叔本华一样,有一个在她看来已经圆满,无需改变的世界。
但这对她来说——还不够;她已经不再痛恨这些人的,几乎,在她看来的,无所作为。
8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tzL3Fb7yL4
噢!如何重新站起——既已见过这地狱之火?
——唯有相信,坚信——也确切地,感受到,她可改变,扭转这一切;回答这不可回答的问题——挑战那不可挑战的源头。
我会回答这问题。她想到,放开这本书,如同释放河流——释放那从天而来的怒涛之海,足以熄灭这地狱火,让它回归到那寂静而壮丽的爱的海原。
ns216.73.216.146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