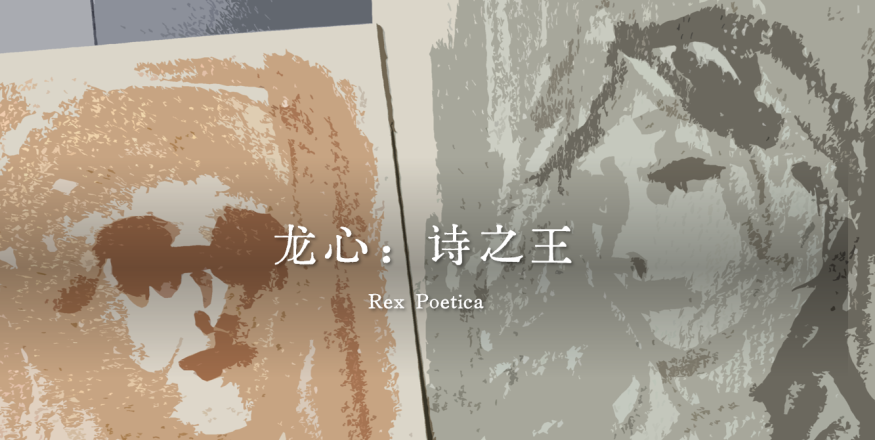“Joyeux anniversaire !”(生日快乐)
经常馨的同学所推荐的云南菜馆距学校直线不足三千米,但因校区西门建在与主道平行的内部小路中,至午时车满为患,后终于左拐上大路后又连续遇到三个红灯,至于三人在车内已和常馨一起点好了菜:林懿文和常桦各点了一份叫做“泡鲁达”的甜品,想来应该是云南一代的特产,海英慈因不爱吃甜品,加上胃病尚未痊愈,婉拒了这份特产。她点了份“黑三剁”炒菜,盖说也是特色菜,附加一份豆腐,一份炒树菇——看到蘑菇,海英慈还是会想到曾经去E所住的城市,同E和E的一个朋友吃菌菇火锅的经历:三个人吃了将近五百块啊!那些菌子可不便宜。因E的朋友据说方才开始做自由创作者,每天入不敷出,最后甚至得将火锅汤打包回去煮菜叶喝,海英慈提议她和E一人各付两百,给她减轻负担,坐地铁回酒店的路上,又给E和她的朋友给买了一个冰镇大福做礼物——送礼物,和朋友吃饭这些习惯,或者说“行为”(comportement)都是E最终言传身教地教给海英慈的,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尽管过去六个月,乃至四年来两人间种种不愉快,她最终决定,恩怨两清,在她的新生活里,她不再继续厌恶她了。
“点好了吗?”林懿文问。海英慈最后看了一眼,吃菌锅的高额款项又回到她脑海。室友主动为她过生日,称寿星无需付款,但她断不想欠个太大的人情。她见主食已够,留下了米线,黑三剁炒饭去除,又看见最后的油焖鸡,想到常桦家中养了鸡作宠物,换成了鱼。
(后来想,应该将肉食去除的。她又因是在社交场合,分神了。)
这样结账下来,约是二百九十元,还算可以接受。
终于在车流中到了这家并不遥远的云南菜馆,海英慈背着书包,推开餐馆的门,如常馨所说,这家菜馆生意火爆,已满座,她寻找常馨,见她从一个隔间中走出来,对着她们三人挥手。
“你们仨这样走进来好像小孩!”
她笑着。常馨是四人里最高的,有一米七二,不过叫其余三人像儿童原因,固该是那气氛,尤其是当海英慈走在前,好奇地左顾右盼时。海英慈幼时曾居住城市里,有时母亲下班后在住宅区对面的“牡丹园”吃饭,小学时的海英慈背着印有蓝色叮当猫的书包进入其中,情景与现下也无二。
“我们几个确实都长得不太像成人——要是换上个校服,谁也不会怀疑我们不是高中生……”
常桦回应。研究生入学半年,寝室四人都越发感“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四人皆差点没能获得入学资格,本科最末颇有挣扎,且年纪皆比正常学业流畅稍长一岁:常桦小学入学晚一年,海英慈本科降转一次,;林懿文因病休学一年,常馨经过了两次研究生入学考试,盖是同岁入学,而普遍思维单纯,保留某种少年习气。
“馨妈妈救我!”
海英慈便跟常馨玩笑,走到她身后,像等待幼师的学员般。室友们多少知道海英慈不擅社会活动,很爱护她,也令她感激。不过,她实际也不是害怕到这个程度,若单独出门,首先是兴致不高,其次是有些难融入环境的寂寥感罢了。她不爱出远用餐,除非是情景特殊:譬去考察城市景观结构时走至远地,就近择店饱腹,又或者,同E见面那次般,因是初次面见,一起吃饭,多聊天交流番……
海英慈摇头。她转头,看墙上的一副傣绣,线条排布出一个少数民族女子的形象。又引她即视感:E便是个少数民族,但其“汉化”程度,恐比海英慈还深。E热爱探索这片大陆东部的各类民族文化,从草原至高原,包括历朝汉式文化的变迁,初来这种热爱几对海英慈而言是不可解的,后来却在耳濡目染中,多了几分对“文化”本身的平常心。海英慈尤记得,她和E初识时,她对E说:“我对中文诗歌鉴赏力很差。”
E说:“但你文章的韵律很好啊,不应该。”
说罢,E分享了一首诗,让海英慈试说感想。海英慈叹息,而后将她全然不解的阐释打了上去。E哭笑不得,回:“看来路路和中文诗有壁。”
至于几年后,海英慈捧着中文古藉寻求兴味,又是后话了。但她每读此类书籍,如当下——见这有少数民族特点的服饰,总免不了想起E来。
“这处桌很好啊,馨你如何找到的?在隔间里边,又僻静又舒适,提前订的吗?”
四人已坐下,林懿文开口说话,海英慈才回神。餐桌位置确实很好,尤使人惊喜是,不像主厅那般吵闹,避人耳目,四人也可边用餐,边闲聊,是她喜欢的方式。倘大费周章出来吃顿饭,却只让她吃到了“粮”,而不曾给她可思索回忆的材料,则太可惜。
“没有,我运气好,来的时候这是最后一桌了,碰巧选到的。”
“那运气太好了!”
三人都道,海英慈也鼓掌:此事在她看来,无异于近来顺遂生活的一种延伸。所有的组成要意似都在这个时间点帮助她,使她能放松而随意,平淡地将一切都处理妥当而不费心思,不再像从前那般艰难而疲劳——乃至当常馨拿出那蛋糕时,她的喜悦神情中所含的礼节性反应和真实心意的界限是不分明的了。
“谢谢馨!”海英慈接过那蛋糕,上插了一根蜡烛。她心中犹疑片刻,想这个数字是否合适——又转瞬感“一”几概括了所有,又有“合一”,“统纳”的寓意,应是可以的。“这是柠檬蛋糕,上面那个是百香果。”常馨知道海英慈不熟悉市面上惯有的甜品,解释给她:“我在路上买的,看了半天,这个最合适。”
海英慈又是连连道谢;她虽然心中又闪过数多思绪,面上的感谢,激动,能做出来则一丝不少。
“来,点蜡烛!”林懿文催促。常桦取来附赠的点火机,给那唯一一根蜡烛燃上了火。
“许个愿吧。”常馨说。海英慈的眼望着那烛火,合上了手掌。
许什么愿呢?
许什么愿才合适?
她闭上眼。幼时,海英慈不许愿:她不相信愿望,也不相信心想事成。一切都只能靠自身努力和外界条件,因此许愿与否,就不重要了。每次许愿,她都在黑暗的末尾,带着几丝恐慌,匆忙补上,“家人健康”的愿望。这是她无法自己努力的,又似得了某个脑海中微弱声音的幽暗的询问:在许愿前,你除了自己,什么也没想到么?
海英慈的父亲说,海英慈小的时候,便和其余人与众不同:因为她曾许了个特别好的愿望。但后来,海英慈“糊涂”了。她不明白了。
“……写作顺利?”她心想。黑暗在流逝,她面上微笑,心里却有些不稳了。
不,太小了。
“让一切都变成它应该成为的样子。”她再许了一个,还是觉得不对,但时间未免拖得太长。虽然海英慈在室友面前觉得自在,也不宜拖延太久。她开始吹蜡烛,一次不成功,几人都笑了, 她也不在意,又试了一次,一边吹,室友帮她唱生日歌。
倏忽,她又想起E了;她想起了她的过去。从前,海英慈总是要硬着头皮帮别人唱生日歌,因为“祝福”和“快乐”,根本不是她的真实想法——但周围的声音是多么纯粹,多么单纯,多么自然。放在过去,她肯定是无法接受的,感到极不痛快。
然现在,她很随意。她鼓起腮帮子,吹那不灭的蜡烛。她想起她学会这件事的过程。
“你真是个好人。”她曾经对E说:“这么真诚地对待朋友。我做不到——是你教会了我如何与人相处。”
谢谢你。
她在心里有些苍凉地笑了一下。人的心态虽常不如我所畏惧那般时刻复杂,从来不是我能想的,世事的根本,却还是像我从来感到的一般,海英慈心想:所有的异样都会爆发,所有的表现都有根底。
“生日快乐!”三人说。蜡烛灭了。海英慈跟着她们一起鼓掌,然后真诚地依次向三人道谢,而云南那儿的甜品,“泡鲁达”,也上来了——原是一种牛奶泡饼干类的食品,据说是从东南亚传至滇地。菜逐渐上,食材新鲜,口味在酸辣和香辣之间。
“像我家乡那边菜的味道。”海英慈说。她心想:还是这个味道更好,重庆菜,虽然味道也不错,却总让她不满足。
她似有那感觉:比起继续品尝那菜系的味道,她不如摈弃对“辛”的依赖,转投清真菜系清淡味道,更让她平静;为摆脱一丝所知不完美的感官,她会毫不犹豫,尽管不是不存疑惑地,逃离。
8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0PmykeULy
“这个餐馆的性价比确实不错。”
“我有种很奇妙的感觉: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其实根本上来说是整个世界上菜品种类和菜馆数量都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了,是吗?比如像纽约,香港,或者什么其余什么地方,”海英慈看着这些成色极佳的菜品,忽发思索:“——我的意思是,最大的人类聚集地和商业圈。”
她坦诚:“我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近六年了,但其实除了在像现在这样的时刻,并无此种确切体验。”
海英慈过的是一种无时不刻企图背离人群的自我流放生活,但她不准备继续拓展这话题;她选了一个更能引起参与者兴趣的方式:
“我想看看纽约是不是也能吃到这个‘黑三剁’——我很喜欢这菜的味道,像我家乡的干豆角——然后看看,贵多少。”
“那肯定贵不少。纽约工资高,消费水平也很高。”
海英慈打开手机搜索,她很快在华盛顿广场附近找到了一家叫“South of Cloud ”的云南菜,提供黑三剁炒饭和黑三剁米线,分别是13.99美元和14.99美元。以当下汇率换算,是这家店价格的三到四倍。
“还算可以接受吧——看那儿的人赚多少。”常馨评论。海英慈关上手机,笑道:“这就是我一点也不想出国的原因。我本科食堂的价格才让我接受,现在改到了三环内,已经贵得让我眼前一黑了。我就想每天用二十块吃饭,然后从早写到晚,不要考虑生计的问题。”
“二十也太少了。”众人都说。海英慈摇头,玩笑为这话题作结:“搞文学搞的。以后可要告诫小朋友,别学隔壁姐姐搞文学,全年无休还得吃空气。”
此语绝非海英慈的真心——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映了一种现实。海英慈极其不擅长社交和理财,也成为了她长久来的深刻困境。她但凡做选择和动了些念头,很可能就是“破财”类,譬如餐桌上这锅酸笋鱼。
海英慈当时为了置换油焖鸡而点的酸笋鱼成了所有点单中唯一剩下的食物——因为那分量实在超乎了想象。她站在那盆鱼面前,花了十秒钟凝神这条因她一念失去了性命的鱼,感受胃中些许不适——她的胃病仍未完全痊愈——然后外出,寻找打包食盒。
(为什么先前没有坚定全素呢?)
她心生惆怅,脑海里浮现出的,倒是另一次吃鱼的经历了:那是和E吃的鲫鱼火锅。两个人一条一条地吃……
哈。真是活在梦里。
她拍了拍额头,决定今后都不犯这错误,回去将酸笋鱼打包,作她明后两日的食物——一是不能浪费这条鱼的性命,二也不能浪费室友的资金。这种熟悉的“不顺遂”感自袭来和结束之间没有间隔多久,盖回到室友之间,海英慈又需要保持笑容,做出那单纯直白的模样了。
结了账,四人走出餐馆外,决定步行回学校。阳光很好,直通校区的大道旁绿化带绿意璀璨。常馨和林懿文并排走,海英慈和常桦相伴,四个人便分这两前两后的队列,分别闲聊。
“我喜欢这些乔木花的配色,有很多给人感觉非常和谐的搭配:像这种绿和白的混合,还有学校中的紫叶李。自然的配色是工业简约无法企及也无法复制的。”海英慈同常桦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以这些花木为概念的墨水……”
“好主意!我其实更喜欢树没有开花的时候,那种浓绿的感觉。”常桦说。
海英慈点头。她听不清常馨和林懿文的对话,又有些困了。众人走了三十分钟,到了最后的宽马路前,常桦又给众人指出了先前应建成商场以解附近众大学无从觅食的燃眉之急的金融中心,四人笑着进行其“不体恤民情”的批斗,遂至学校。几人并陪同常桦去取快递,海英慈等待时,打开手机,并无特别想念,几是无意识地,点开了E的主页。
8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6wHymvkhd
“……英慈?”
8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bGi9wpoTJM
海英慈抬头。她面前是片凸面镜,可映出她眼周骤然变色的神情——一种褪去了温和,随意和闲适的真实浮现——令她的瞳孔深黑而扩散,隐有震颤。
“噢,你们看,我们四个都在里面呢。”林懿文指着那凸面镜说:“一起拍个照吧!”
海英慈的嘴角抽动,但最后转变成了微笑。
“好。”她笑着说,切出相机,赞同这个提议:“应该合影,给我妈妈看看我最好心的室友们——她会很欣慰,我终于能和室友们一起出去吃饭了……”
四人抬头,拍了张照。海英慈可看见所有人在凸面镜变形的身体和显著的笑容。她看见三个室友纯粹而明亮的笑容,和她自己唇边的犹豫。她没有皱眉,但心中盘旋着一种不快:还是和从前一样。她的笑容中带着一种阴霾——有一种背反的森然和阴郁埋藏在她介乎玩世不恭和心怀叵测的笑容中,使那看上去——几是恶性的。
“……这是你的报应。”
忽然,她又听见E对她所“说”的那句话。海英慈背过身,放下手机,深呼口气,复转向室友,和众人一道回程。
ns216.73.216.81da2